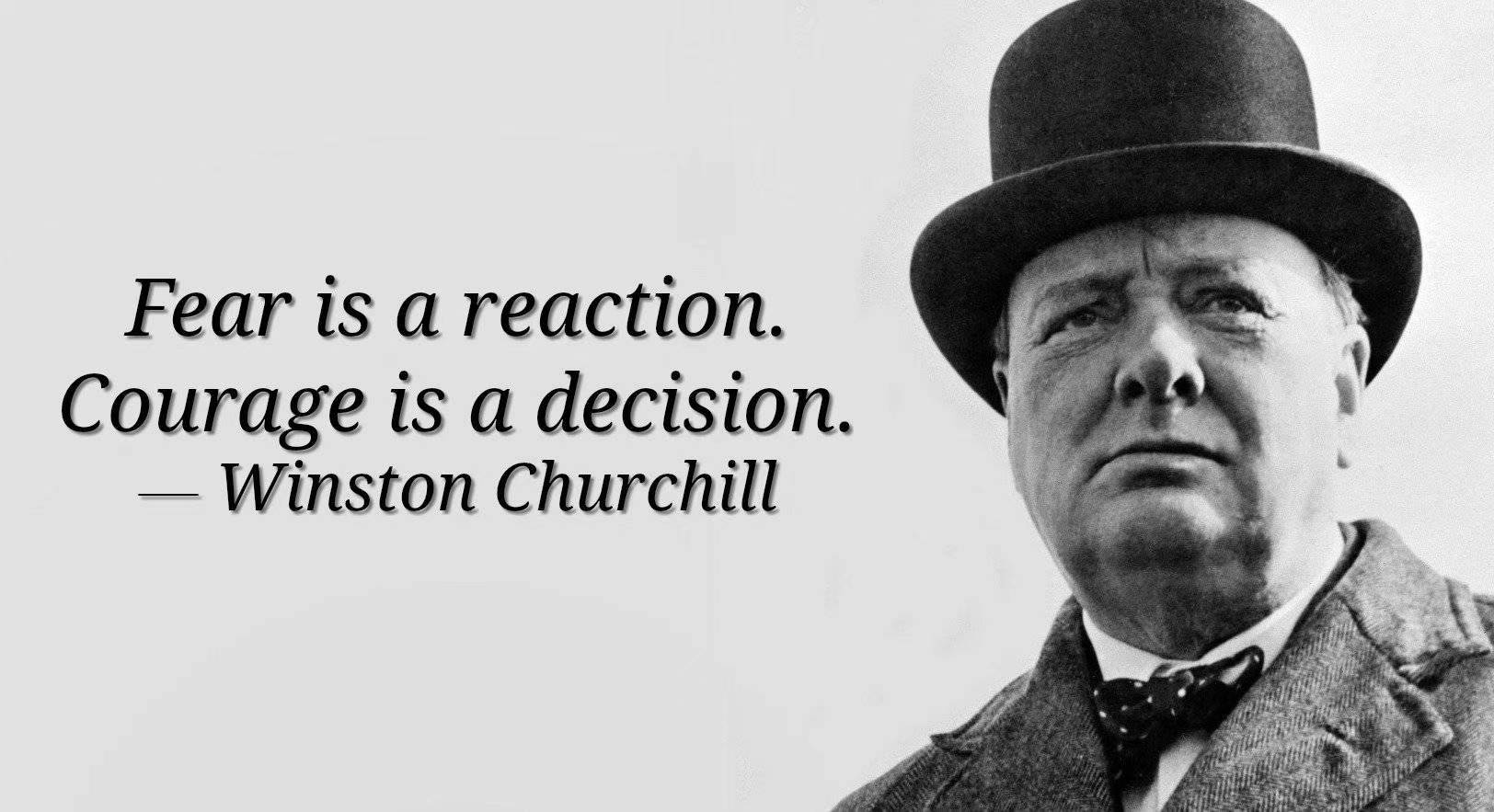“什么是活在真实中 living in truth?就是不违背自己的存在”———来自二把刀的信
1949年1月沈从文在“精神失常”期间,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接他到清华园过年。
这顿年夜饭沈从文吃得相当苦涩。此时北平解放在即,在座的人笑语和辩难都是在“解放”意义下进行的。只有沈从文在听窗外炮声,想象无名士兵的哀乐。客厅里有宗教气氛,人人都在“信”着某样东西,而他是个“我思故我在”的人,如果不思,则存在没有了,剩下一个沉默,羞怯,屈辱的十七岁的人格,盖在微笑之下。
他说,以林徽因的明敏也没有查觉。林徽因真是不能查觉吗?林徽因的客厅一向是沈从文的避难所。此前二十年,沈从文一有苦闷马上向林诉说,如孩子般流泪,得到她母性的同情和热烈的安慰。
这一次她却带着关切的责备“你想的却是‘你’,为什么不来用笔写写‘人’,写写一个新的人的生长,和人民时代的史诗?你有权利可以在这个时候死去?”
他微笑。这间客厅里,他屡屡想到走投无路的三十年前的大年夜,唯一帮助过他的陌生人是一个黄昏串街卖煤油的老头,曾借给他两百铜子,使他度过了一个年关,这份善意化成了他文学里永远的柔情,“这就是《边城》的老祖父,我让他为人服务渡了五十年的船。”
贫苦还有人同情,忧惧却无人可说。老渔夫没有了。他说,“只能见彼岸遥遥灯火,船已慢慢沉了,无可停顿,在行进中逐渐下沉。”弃船算了!狠下心往下活。我干过,沈从文也干过,他不是跟随时代潮流也写过《老同志》么?虽然结果他早知道,“这么写算完了,不这么写也算完了。”死路一天,不,死路两条。
真正的绝望很平静的,火气全无。就是在这样的心情里我才读沈从文。同坐那间客厅里,当梁林在谈未来万千工人的新集体房屋如何设计,如何和工厂大烟筒遥遥相望时,我跟随他视线,以沉船上的人奇异的平静,在看客厅里一只四方几,台子上的北齐雕相和唐代小白陶猪,北魏小铜金刚。
他写,“我在认路,一条回向过去的路。”难怪他转向古代美术史。政治侵犯了一切,剩美术里还留有一点点真的生命,他看到一个小铜匠敲打银鱼时如何为心事流泪,一边敲击,鱼的纹路里带着人性的颤动。
沈从文,容我这样的二把刀,对你抱拳!今人无可谈,古人来相亲。
回到林家客厅。当夜九点,放着贝多芬的音乐,别人在谈话,沈从文躺在沙发上听。
索性,我来抄一抄这段沈的话,“我躺着,觉得身下不是沙发…春天阳光下,庙里的罗汉竹,戏台前空地上有人在搓丝线,二十个小小铜纺锤在一个小竹架子旋转,旋转复旋转,城中即有了丝线铺,城里城外年青女人即有了一方一方绣花围裙,有了枕头帕,花荷包,组织了一个区域的平凡哀乐人生。大河水在暗中涨泛了,谁也不知道从多远地方落了雨,好一片豆绿水!水上了沙滩,两岸人到时都乱了起来,为追捉鱼虾,和上流漂浮而来的木材和牲畜,到处是召呼和笑语。沿河都有人扳罾沉网。什么人的风筝断了线,向远处飞。有人牵了马匹却看扳罾,一个不留心马从大路上溜了缰,向野处,向自然,沿河狂奔而去。所有远近顽童都为这件事而拍手。竹林接着竹林,一片绿接着一片绿,竹梢上就有许多断线小风筝悬挂。竹林前后一些小房子间隔一些小房子,排列在河边,到处有生命哀乐,和那个常与变…”
我从前不喜欢沈从文,觉得多情近于贾宝玉,行文近于民歌,笔下世界狭小,一泓清水而已。但假如有一天你也身心交困走投无路,读一读,一个字一个字读,读出声,你当可看到那水清而深, 仿佛进入时间的深流,你如船飘浮起来,如在梦中,又仿佛真真切切触到什么东西(包含了自己)的根,非常静谧。
写了这么多,就是想替你回答那个问题:什么是“活在真实中”?就是不违背自己的存在。随信附上沈从文在1957年5月1日,为劳动节外滩的游行队伍画的速写,一只做梦的船,在大海中起伏。画旁边他写着“在红旗的海,歌声的海,锣鼓的海里,总而言之不醒。二把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