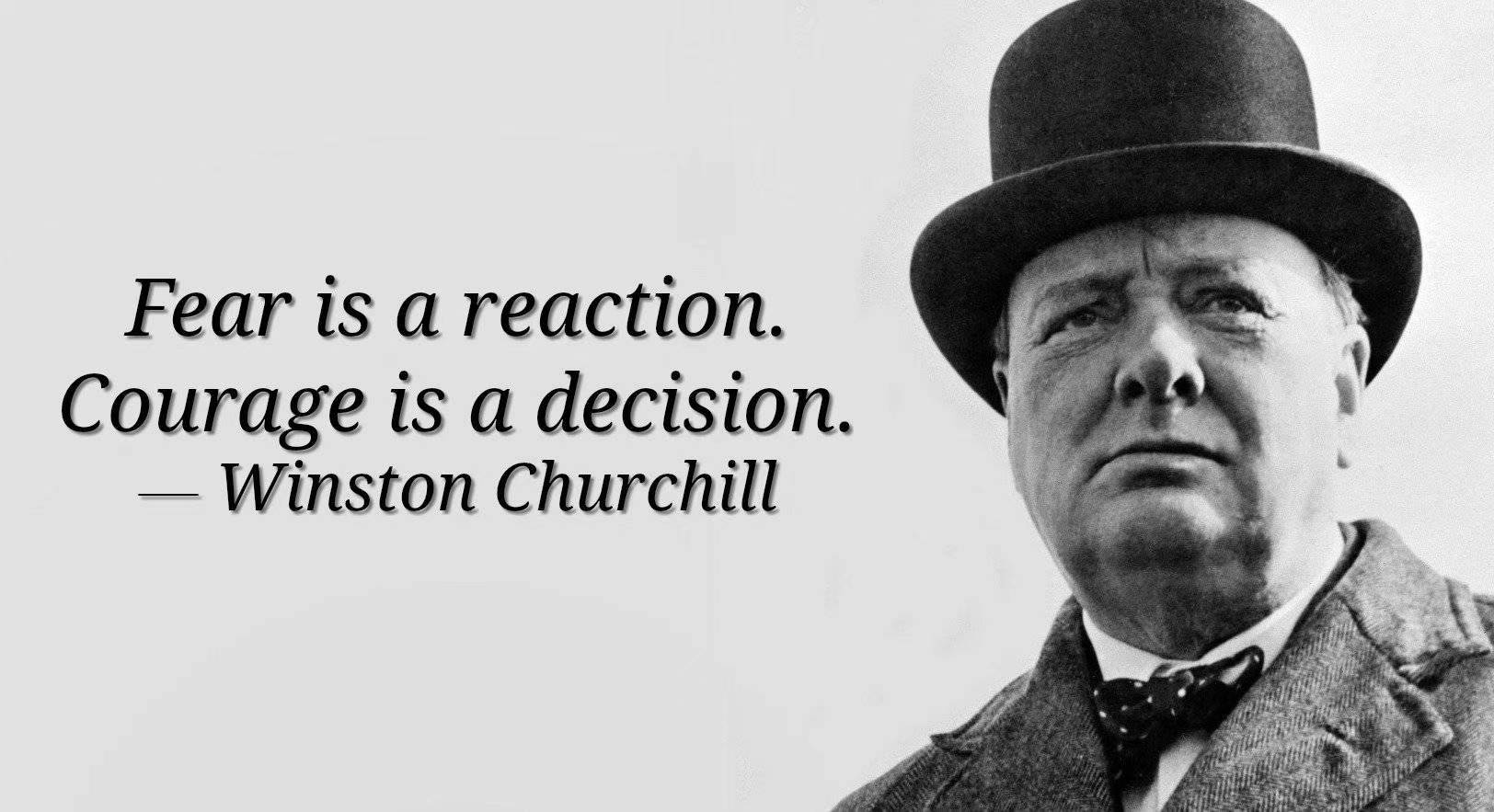什么是哲学?
我的定义是,哲学是对抽象概念的解析。
抽象概念最初就来自直觉,我们的感受。
随着思考的深入,抽象概念被定义,最先以语言的方式表述出来。客观存在里的河流在意识中的投影从此被河流的文字指代。
随着抽象概念的明确,以数学为工具,科学脱胎于哲学诞生了。
不同的人,有不同的阅历和经验,也有不同的敏感程度。看同一个事物,会有不同感受。你看到过苹果,在听到一个哲学家描述了苹果的特征之后,你也就很容易明白了苹果是什么,而且因为你独特的感受,对于苹果,你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描述,很可能有更好的表述方式,甚至发现更多苹果的特征。
如果哲学家们说的熊猫概念,你完全没有看见过,那么就记住哲学家说的熊猫的特征:黑白熊。保持着一份怀疑,等你哪一天真看到了熊猫,就会立刻明白哲学家们说的熊猫是什么玩意儿了。这时候,请还是保持一份自信地思考,不要忘记说不定你会发现一些关于熊猫的新特征。
举这样的例子,想说的是:
哲学是不需要刻意看论证过程的(千万不要去咬文嚼字),结论重要得多。记住结论,保持着困惑。那些你没感受到个概念,你是无论如何读不明白的。不必花太多力气。而等你保持着漫无目的的思考,顿悟到它的时候,你会发现其实那个哲学家所描述的概念或理论模型,并不神秘(颇有些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)——真正让人头疼的是人类思维。
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。请不要迷信“阅读原著”的说法,晦涩的翻译文字远远不如思想史万有引力、小播读书这样的哲普来得有力量。
最后我想说的是,几千年来,西方的的哲学家们所做的并没有实质上的创新,他们一直在做的是以认知为变量,解释着同一个存在(这里的存在,包含着意识)。所以请放心大胆地以思考存在和意识为起点,开始自己的哲学之旅—–保持着自己的独特视角,做一个世界的观察者,享受人生的旅途。